图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卫星研制人员正在聚精会神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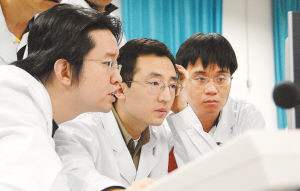
图 2. 11月26日,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

每次火箭到靶场的时候,孙岳都特别紧张,生怕出问题,不过他说,“压力逼得你只能去想办法解决,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尽管压力那么大,但孙岳说:“我还是爱这个工作,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没有羡慕过别人。”
在“嫦娥”研制队伍中,有不少像孙岳一样的年轻人。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介绍说,绕月探测工程有近百家单位万余人参与其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这支队伍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年轻人多。
30岁不到的主任设计师,30岁出头的总体设计师,40岁出头的总指挥,随着嫦娥探月梦想成真,各个系统的年轻顶梁柱走入了公众视野。
时势造英雄
在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航天工程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嫦娥一号”卫星研制团队40岁以下青年占71%左右,平均年龄不到30岁;托举“嫦娥一号”卫星升空的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试验队共188人,40岁以下人员占到60%以上。
龙江,34岁,“嫦娥一号”卫星副总指挥;孙泽州,37岁,“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饶炜,36岁,“嫦娥一号”卫星总体主任设计师;岑拯,43岁,长征三号甲火箭总指挥;陈闽慷,35岁,长征三号甲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这就是“嫦娥”队伍中的“少帅军团”。
是什么让这么多年轻人站在了重要的一线岗位上? “是历史把我们推到了舞台上。”长征三号甲火箭总指挥岑拯说,“在这个领域,我们上面都是60多岁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人才断层,接下来就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
岑拯是湖北浠水人,1989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工作,2004年开始担任长三甲火箭总指挥。 “当时也挺突然的,本来我是副总设计师,按常规晋升的话应该是总设计师,然后才是总指挥,后来领导决定,就一步到位吧。”
除了“文革”造成至少10年的人才断层,20世纪90年代,航天人才也流失了一部分。那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初步勃兴导致收入分配制度严重失衡,在那个被形像地称之为“脑体倒挂”的时代,确实有无数的案例证明:“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黄欣今年36岁,是领衔攻克紫外月球敏感器技术难题的副主任设计师。他说,1994年他参加工作那阵子,一些技术人员纷纷放弃了清苦的研究工作,跳槽、下海,跑到南方去经商。 “所以现在50岁左右的研究人员很少”。
另外,近些年来,型号多、任务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明确规定:在型号研制队伍中,35岁以下年轻人要占到1/3以上,对政治素质好、业绩突出的优秀人才要大胆使用,破格晋升。这种机制给年轻人提供了展现自己的舞台。
“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36岁的孙泽州说,他1992年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时,型号少、工作量小、任务轻,年轻人很难有机会。 “这些年型号任务多了,大家承担的任务也重了,对每个人来说,机会都多了。”
越是不好走的路,越想走一走
国际上走在深空探测最前沿的国家,进行月球探测的第一步往往选择“撞”或“掠”,就是利用撞向月球或者从月球身边掠过的时间,对月球进行基本的探测,而“嫦娥一号”卫星的起点是“绕”。
以前研制资源一号卫星时,有不少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坐镇,而“嫦娥”研制队伍以年轻人为主,大家的经验都比较少。
“越是不好走的路,就越想去走一走。”孙泽州担任“嫦娥一号”的副总设计师时才33岁,他坦言,刚当副总设计师那会儿, “心里总打鼓,原来我干测控工作,现在当副总师,很多专业领域还不熟悉,感觉还要补课。”
就一次航天任务而言,可靠性永远是被摆第一位的。因此,每次航天任务的绝大多数器件都是继承以往成功的工艺,只有在保证万无一失的前提下,才会允许创新。当然,哪怕只是一点儿微小的创新,也要经过最苛刻的检验。
但这次在“嫦娥一号”卫星上,有一个器件却是一件崭新的产品。不单是在我国,它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第一次被使用,它就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控制与推进事业部光学敏感器研究室研制成功的紫外月球敏感器。
“人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光学敏感器研究室主任卢欣说,2004年2月,“嫦娥一号”卫星正式立项,光学敏感器研究室正式接到了研制“嫦娥一号”卫星控制分系统光学姿态敏感器的任务。领导班子经过反复考察决定启用新人,任命年轻的高级工程师黄欣和武延鹏分别担任两支研制小组(紫外月球敏感器和中等精度星敏感器)的主任设计师和副主任设计师。
“搞新东西,绝对不会轻松,只有充满荆棘的路。”36岁的黄欣说,他们团队在研制道路上就碰到过大麻烦。
紫外月球敏感器的成像器件是CCD,当黄欣他们按照英国CCD生产商提供的器件手册设计了电路后却发现,根本无法成像。
“那是他们公司的新产品,他们的技术人员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黄欣说,从2004年1月到7月,他们整整攻关了7个月,最终解决了问题。
经过反复摸索,他们还充分运用了CCD所有功能,并使CCD最短曝光时间缩短到只有几毫秒甚至更短,将曝光时间调整范围扩大到了120倍,全面满足嫦娥一号卫星的使用要求。 “我们告诉英国生产商如何解决问题后,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2006年12月,紫外月球敏感器、中等精度星敏感器等关键部件在预定期内成功交付。此次“嫦娥一号”卫星上,这个研究室贡献了16套共17件产品,并有多项创新。而这个研究室64名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
“按照国际同等水平,关键部件的研制从原理到应用至少需要五六年时间,但他们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任务。”该研究室书记杨涛说,年轻人就是喜欢挑战,在挑战中他们挑起了大梁。
麻烦随时会冒出来
当卫星在环月过程中随月球进入地影时,太阳就照不到卫星上,卫星就失去了能源和热流。 “嫦娥一号”卫星处在阴影区有可能会长达5个多小时,月食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卫星会被冻僵。
此外,月球红外还有可能将“嫦娥一号”烧坏。月食和月球红外这两个难题对热控系统提出了考验。
为了解决这个以前被忽视的问题,“嫦娥一号”卫星热控主任设计师邵兴国尝试使用三只舱外安装的U热管,对卫星上安装两蓄电池组舱板进行热耦合设计,同两舱预埋的热管形成耦合热管网络系统。
这是首次在卫星热控设计中采用的技术方案,但已经来不及在初样试验中进行验证。邵兴国带领其他设计人员多次深入热管生产车间和热管装配车间,一起解决工艺问题,最终在正样热平衡试验中得到了验证,解决了这个难题。
月食问题也让“嫦娥一号”定向天线分系统的主任设计师孙大媛遇到了攻关难题。
之前的天线都是单轴的运转模式,无法适应“嫦娥一号”卫星的特点。孙大媛和同事查阅了大量资料,做论证、试验,最终设计了双轴天线。然而,就在初样转正样的时候,麻烦来了。零位传感器原定可承受的最低温度是零下50摄氏度,而在月食期间最低温度可达零下65摄氏度。此时,距离最终评审只有1个月了。
孙大媛跟同事开始重新考虑,以前的设计中散热措施比较多,现在以保温为主,把零位传感器能包裹的地方尽量用特殊材料包裹起来,保证温度不会太低。
他们争分夺秒,直到开初样转正样会的那天,试验结果出来表明符合要求,才终于松口气。
技术落后,只能拼人力
这群年轻航天人的繁忙程度,是出乎很多人想像的。
孙泽州有个原则,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初样工作量大,如果出现意外,就要忙下半夜。 “有时候晚上10时下班,大家会觉得下班挺早啊!”
从2003年开始,孙岳进入了工作以来最艰苦的阶段。这几年每年“五一”、“十一”他都没有休息过,春节也就只能休息三四天。工作也不是做完一个再做另一个,往往要同时开工。
记者采访火箭发动机副总设计师段增斌时,他刚做完一个实验,由于工作程序很紧,他前一天晚上忙到了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又开始忙活,一直干到下午2时15分,午饭没来得及吃,还要开会讨论,继续实验,又一直做到很晚。 “不要说吃饭了,忙起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武延鹏2004年刚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今年才30岁。为保证他们团队研制的中等精度星敏感器视频电路的成像效果,他每年都要随研究团队前往河北省兴隆县观星站做整机观星试验。
观星站设在山顶,海拔近千米,条件很简陋。为了观星方便,还要在开放式屋顶下工作。在冬天,室外气温接近零下20摄氏度,山风又大,“冻得温度计都不显示了”。年轻的科研人员穿着棉大衣,常常从晚上七八点干到第二天清晨5点。有一次,武延鹏在大衣兜里揣了瓶矿泉水,拿出来时都冻成冰块了。
五院总体部综合测试中心,承担着“嫦娥一号”卫星整星综合测试系统方案设计任务。经常进行的模飞测试及大型试验,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整个系统都不能断电。综合测试分系统岗位多、人员少,有的岗位经常是两班倒,工作12小时,休息12小时。夏天电源设备的发热量又很大,使得原本就很紧凑的测试厅如同蒸笼一般,时间一长,连喘气都费劲儿。值夜班的人为了防止自己打瞌睡,不得不使劲儿喝咖啡。试验任务圆满完成后,很多科研人员的生物钟被打乱了,感到疲倦却总也睡不着。
2006年春夏之交,整星热试验开始,饶炜有时24小时都不休息,时刻关注跳动的数据。 “如果有一刻不盯着,心里也觉得特别不踏实。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一连好几天都做同样的梦。只有最后把问题解决了,心情才会轻松。”
黄欣说:“‘嫦娥’任务技术难度大,型号多,因为国内科研技术水平相对而言还比较落后,我们只能拼人力。技术手段差一点儿,就要靠多投入时间、精力,尽力做到更好。”
爱国大于爱家
过了3个本命年的黄欣还没有小孩,只因为他妻子也和他一样,都是航天人。
“本来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计划要个孩子,但那正是“嫦娥一号”任务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一直耽搁到现在。”
黄欣的妻子在制导导航控制分系统工作。在“嫦娥一号”发射前两个月,她就去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10月1日从西昌回来在家待了3天,又一头扎进了北京航天飞控中心。从那以后,他们俩在北京航天飞控中心见面的次数,远远多于在家见面。
“两边的父母虽没把这个事情挂在嘴上,但我们能感觉到,他们比我们更着急。”黄欣说,“嫦娥”任务完成后,会有一年的时间相对宽裕,到时候就准备要小孩了。
37岁的胡剑平,是“嫦娥”语音存储装置负责人。 2005年12月,上级单位决定在“嫦娥一号”卫星上安装语音存储装置,并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样机,4个月交付正样产品。临时受命的胡剑平就说了一句“保证完成任务”,就克服了重重困难,准时交付了正样产品。
岑拯说,2000年前,每次发射任务,他都要出去两个月,孩子只好让爷爷和姥爷带。现在型号多,高密度发射,他经常有半年时间要待在外面,更难照顾家里。 “这种状态不是我个人的,整个航天队伍都是这样的。”
五院的科研人员戴居峰,孩子刚出生不久就去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他想看孩子,只能让同事帮忙拍DV。
他的岳父曾经对此非常生气,哪有忙事业忙到小孩都不顾的。戴居峰因保密要求一直没有向家人透露他从事的具体工作,后来,当岳父知道他在为“嫦娥一号”任务工作,异常激动,连声责怪他为怎么不早说,要他安心在基地工作,说家里一切都会照顾好的。
邵兴国觉得,国家培养这么多年,需要航天工作者自觉自愿投入自己的精力。 “我一直觉得这是职业所在,职业要求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他认为,从事航天事业对国家、人民的贡献体现得比较直接。 “工作是普通的工作,也没有多崇高,但工作本身对社会影响比较大。尽管工作比较累,还是有这个信念支撑。”
“我听说,我们国家能够买到的搞不好,引不进来的东西却基本上能搞上去,比如火箭、原子弹等,其实都是逼出来的。”段增斌说,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我们的发动机承担过104次航天任务,保持着100%的成功率,动力系统这么复杂,我们都能做到首屈一指,独此一家,没有点航天人的精神是不行的。”
11月26日,在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之际,新华社发表评论说,从“两弹一星”、神舟系列载人航天工程到“嫦娥一号”工程,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催生了一支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一大批年仅30多岁的业务骨干在探月工程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航天事业未来的希望之所在。 (中国青年报崔玉娟/叶铁桥/赵飞鹏/李松涛)
(来源:中国青年报)
——————————————————————————————————————————————
大陆科技落后的原因是起步比别人晚了50年,

而不是智商或者受教育的程度!

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饱受屈辱的民族,注定我们要适应更恶劣的环境~












